2021年1月17日,崇实·第79期《傩面》读书会在都匀万达崇实楼台书店举行。作家、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肖江虹,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贵师大文学院副教授索良柱两位嘉宾同40余位书友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推文以飨读者。
肖江虹:像读书会这种高度仪式化的属于文学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里越来越少。
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在都匀这边有很多文学上的好朋友,我写作刚出道时就和孟主席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叫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其实什么都没有写出来,文学院的院长苑坪玉老师带着我们这群所谓的作家,在贵州范围内采风,真的很幸福,很少有那么一群人聚在一起自由、兴奋地谈论文学。
刚开始写作的时期,是我生命里文学的黄金时期。写的小说要是发表在了哪怕不起眼的刊物上也会很兴奋,然后奔走相告。写到现在往往会有浓郁的疲惫,我最近2020年在《十月》杂志发的小说《美学原理》被《思南文学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样刊寄到我家,到现在连样刊都没有撕开。文学最幸福和最兴奋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像现在一样,和许多朋友坐在一起讨论文学,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和孟哥在文学院的时候去采风,晚上所有人都睡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文学,讨论到凌晨三四点钟。现在我们聚在一起,从来不会讨论文学,都在说日常。像读书会这种高度仪式化的属于文学的时刻,在生活中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时刻,非常感谢大家,在寒冷的天气里来到这里讨论文学,让我感到很幸福。
文培伦:看完《悬棺》,做了一整晚关于死人和下葬的梦。
看完《悬棺》,百度了一下真实的悬棺,做了一整晚关于死人和下葬的梦。先是梦见一个小孩带我走进一个像体育馆建筑的葬墓群,脚下全是泥水混杂的小路,又无比阴森。后面又梦见我奶奶去世了,在她下葬的旁边发现有好几处也在下葬的人家,一片繁忙的景象。再后面还吹起了《百鸟朝凤》来。完全沉浸在作者描写的世界里,还做了那么多的梦,我想是作者的故事讲的太好的缘故。
为什么会感觉如此真实?我觉得一是叙事的水平高,总是牵着你走,像《傩面》的女主角,到底得了什么病?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到底从事什么职业?所有这些牵着你不断向前,最后居然也不得要领。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问了一下肖主席到底怎么回事?说放了那么多蛊,一个也没解。然后他告诉我其实是无解的。
二是生活的场景太熟悉:秦安顺在回忆他父亲母亲相见时的情形,那种初见的面红耳赤的情形令人心动,到最后的时刻,父亲人之将死躺在床上,他母亲说要死早死,折磨人,看你这样,干脆自己死了得了。这人生大概也都如此,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肖江虹:其实不是相爱简单,相处太难。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相爱的,也是这样相处的,交流基本靠骂。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交流方式,不能认为这种交流充斥着野蛮暴力,相反它充满着温情。他骂你这个狗东西为什么这碗面还不吃?前面所有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吃,这是相处的一种方式。
余钢:独具匠心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是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余钢。上一期索博士主持的《百鸟朝凤》,我曾经给大家分享了肖江虹《百鸟朝凤的张力叙事》,后来又研究《傩面》,写了肖江虹小说《傩面》中的魔幻叙事。
因为我看了很多人的观点,像索博士,他都是从民俗叙事的方式来研究肖江虹老师的《傩面》,我发现他的民俗民风三部曲《蛊镇》《悬棺》和《傩面》,《傩面》主要是受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所以我就写了这篇论文,当时写作的时间是2018年以前,没有想到后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所以后来索博士他知道我写了这篇文章,把文章收入了贵州师范大学今年的学报的第一期。我认为《傩面》和其他作品,最关键的就是民族叙事,即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的魔幻叙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法都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又体现了贵州边地的乌龙文化的神秘梦幻色彩,两者奇妙的结合,造了一个幻化的世界。
因此书中人物形象就具有魔幻性,如《傩面》中的秦安顺,他是傩村最后一个傩面师,是乡村世界最后的守护者,同时他能化身各路神灵与鬼魂对话交流之外,他还有其他的通天的本领,会唱各种傩戏。所以说通过塑造傩面师秦安顺这一充满魔幻色彩的人物形象,在一张张神奇的傩戏面具背后,看到的是贵州边地独特的乌龙文化,感受到的是傩面师的乐观淡泊而又珍视生命的人生观。
在叙事手法上打破了生死的界限和人鬼神的界限来描写。另外还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时间叙事的影响,围绕着傩面师秦安顺这一具有魔幻色彩的主人公,设计了一个圆形的时间结构,秦安顺他个人的生死轮回就是如此。已经接近死亡边缘的傩面师秦安顺,戴上了傩面面具后,先后看见了他的父母的相亲拿话(提亲)、结婚怀孕生子的情景。在临死之前他又戴上了伏羲傩面,回到了母亲临产之际,见到是一声清脆的啼哭,所以现实中的秦安顺死后,万籁俱寂。因此说他采用了拉美魔幻主义循环时间的叙事和中国的轮回时间观。
另外他还表现了神话的叙事,贵州边地古老的村庄存留着原始诡异神秘的自然景象,蕴藏着丰富悠久的神秘的仪式和神话传说。《傩面》所描写的傩村就是一个神秘的村庄,这个村庄常年弥漫着浓稠的雾气,富有一种神话的色彩。
所以研究《傩面》中魔幻叙事可以对贵州民间乌龙文化的开掘与关注,以及对中国文学神秘趣事和生命书写的表现和继承,对小说美感特征的提升。所以这一部以贵州边地民风民俗为写作题材的小说,运用了魔幻叙事的写作手法,反映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与传统崩塌过程中书写世道人心,是一部具有独特审美风貌的魔幻性主义小说。肖江虹先生在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艺术的基础上,创造性的继承发扬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创造出了独具匠心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王子玉:是否有意运用细节勾连起了这三篇小说的人物或文化内涵?
余钢老师主要从理论方面做了梳理,我不太善于理论方面的探讨,就简单的谈一点自己阅读的感想,跟作者本人还有书友的交流一些问题。
首先提一点相关的题外话,之前肖先生提到文学,我本人也是从事文学方面的教学,细想发现,闲暇之际,跟同事、朋友,平时讲的也多是生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又细想了一下,可能也不是21世纪才有的情况。19世纪初,英国很有名的女作家简.奥斯汀,她的代表作之一《傲慢与偏见》在我们国家读者群里面广泛流传,在那个时代就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对于19世界初的女作家而言是很不错的,并且文学地位也很高。后来看到国内高校的一位教师,他直接阅读了国外出版社汇集的简.奥斯汀与姐姐的通信。
她终身未嫁,生活的交际范围也不广,和姐姐的通信的内容让这位教师很失望。信里面没有谈他感兴趣的文本写作内容和重大的社会现实评价,两个人的通信写的都是一些镇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实际上我觉得从女性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对于简.奥斯汀不够了解,甚至包括刚才肖先生讲的对人性了解的还是不够透彻。大部分人,不管是大作家,还是一般的阅读爱好者,不太可能一天或者一生都在关注文学这个问题。
话又说回来,如果完全没有文学或者生活中一点仪式感都没有,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是一种最佳的方式。圣经上说‘阳光底下无新事’。这不是这个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或者说文化带来的问题,也许就是人性本身的问题,并且可能也是一桩普通的常见的事。
在读小说时,小说文本前面还绘制有一个群山图像,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三篇小说算中篇,其中涉及到的三个地名汇集在一起:蛊镇、傩村、《悬棺》涉及到的燕子峡,还有一个曲家寨,我不知道设置曲家寨跟来辛苦的这一宗族,是不是两个村寨的?可能是都住在燕子峡的两个宗氏吧(肖表示同意)。
不知道肖先生原来有没有构想,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形式精巧的,可能是一种不太好的阅读趣味。比如说三部曲,在主题的文化内涵上肯定是有勾连的。在形式和作品内容的勾连上,我发现了一些细节表现:一处就是蛊的镇王木匠,他后来对赵锦绣产生了感情,他是木匠,工作当然包括制作棺材。第二处悬棺里面,叙事人‘我’14岁定了一副棺材,制作棺材的是王木匠,另外还谈到了他二婶,二婶是蛊镇嫁过来的。就是这么几处勾连,把作品里的三个地方组织在一起,至于傩村,没发现有细节勾连蛊镇和燕子峡。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阅读趣味,作者本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对于细节和主题升华方面的勾连,就好比上一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三部曲,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蓝》《白》《红》,三部曲的几位主人公,最后都碰巧在一次海难中获救,一一经过镜头,影评说这是看似意外巧合,却是对三部曲主题文化意蕴的升华。想请教一下肖先生是否有这种意向,运用细节勾连起了这三篇小说的人物或文化内涵。
肖江虹:一个好的作家,要学会从“恒”里边儿去找出“变”,然后把变表达出来。
读得很仔细了,这三个故事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前两个小说在我看来是没有联系的。但我要做一件事儿,当我在写第二个小说的时候,在精神上,在深度上哪怕一丁点的往深处继续挖掘,当然,这是小说最难的部分。
写到第一故事时就准备放弃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他让我写篇小说,于是就写了《蛊镇》,他说还有点意思,要不再写一个,又硬着头皮写了《悬棺》。他说什么事都应该弄三个才可以。写第三个的时候整个人要崩溃了,它们的内核是高度相似的,都是讲边地非常神秘的民俗民风。在这个基础上后一个小说要在前一个小说有一点进步,这是非常困难的。那段时间写《傩面》,经常跟良柱在一起探讨从哪个角度可能会比前两个在深度上有贡献,非常困难。
你说的这些勾连,并不重要。前两个小说那些人、事,他是作家在创作里边的一种不自然的勾连,这种勾连只是单纯记忆上的勾连,它跟创作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三个小说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有关系,也从来不认为我有什么三部曲。
其实良柱还不是太满意,他说其实应该再写一个长篇小说,把所谓的边地写绝了,让别人不再写了。我也做不到。让我再弄一个长篇,还要在这三个的基础上有进步,那会把人逼疯的。之所以将三个小说放在一起出书,其实就是因为文本内部的气息有一致性。里面一老一小的设置突出的是两个词:变和恒。
在每天的生活中会发现我们现在处于高度同质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模式很相似,买一样的菜,坐同样的公交车,走的同样的路,看同样的建筑,每天从单位到家,甚至连玩的公园都是一样的,这是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敏锐的人,对生活细致、具有洞察力的人,你要从不变里把变找出来。
在小说里面说到过看不见的变,不要认为天上的北斗七星,那几棵松树永远都是在那个位置。它们位置一直都在变,凭肉眼是看不见的。作为一个好的作家,你要学会从这种“恒”里边儿去找出“变”,然后把变表达出来。所以简单的看,小说里的一老一少,跟文化、心理、地理意识有关的“恒”的可能是一样的,但“变”的那部分是不一样的。
索良柱:阅读贵州本土作家,从地方理解中国。
《百鸟朝凤》读书会后书友们就在期待了,今天终于成行落实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现在感觉我完成了一件大事。其实我的理念在崇实也讲过,文总当时推荐书是没有考虑贵州的,他特别迷信豆瓣的评分,分数越高就越觉得经典。当时我说试一下我们本土的作家,比如肖江虹、冉正万,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近几年提的一个说法叫:从地方理解中国,地方是理解中国的一条捷径。
当时我看到肖江虹特别兴奋,研究文学的人,你发现如果所研究的作家全部都是外省的,都离你很遥远,是有点绝望的,你会觉得很寂寞。我记得有个老师说我眼光很好,很早的时候就天天讲肖江虹。我还在上海读书时,在《中篇小说选刊》上翻了很多小说,都没有记住,刚看完《喊魂》就记住了,虽然小说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作家前途无量。
我想作为一个评论家,读书也是一样,看人看事要准:就是你刚有一个苗头,我就可以判定你一定是大有作为。当时余华的《18岁出门去远行》一出来,真正优秀的评论家就已经下定论说这个就是中国前途无量的作家。所以当时我看到《喊魂》时特别兴奋,翻到作者介绍的时候,贵州和贵州师范大学,我一下觉得自己也有光,我也是师大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看好他,而且我也觉得有一天可能会认识,肯定能成为好朋友。果不其然,在一次吃饭中,我们一见如故。因为他也寂寞,人到了一定的高度也寂寞。最近省外的一些评论家写的评论,根本就读不懂,他们读的太离谱了。这种对作家来讲也很悲凉,没有人能理解作品,甚至已经完全反了,这是很荒谬的,但在评论界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
我看到说像美国的评论家,他一辈子大概只跟踪5位作家,目的就是要准确的理解他,要在准确理解作家的基础上进行解读,而不是完全跟作家意思相反。国内的评论家对肖江虹的作品就有很多误读。
不仅仅是对肖江虹的作品,我的建议是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地方,从地方出发去理解中国,你会觉得无比的亲切。
书友A:我和大家的理解可能不一样。阅读之前不是很了解肖老师,我也是带着好奇的心理来读的。心中有很多疑问,包括蛊术这一块,我不是贵州的,但是听说过蛊术,说是在黔东南那一块是有蛊术的。我想知道蛊术到底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还是封建迷信?所以想让肖老师介绍一下什么叫蛊术。你当时写蛊术的初衷是什么?想表达的是什么?
第二个是《傩面》,我不太关注女主得了什么病,可能是难以启齿的病。我关注的是秦安顺把面具拿下来后,就是现实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复一日,戴上面具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的父亲、母亲,能够让他感到最快乐的时光,我想知道,您写《傩面》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肖江虹:修辞立其诚。
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说一部好的小说,作者是说不清楚的。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被很多虚假文学的叙事伦理误导了很多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散文,叙事的内在的情绪是非常虚假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小学的语文教学里,作文是这么教的,说半夜十二点半经过老师的窗前,老师的灯还亮着,还在给我们批改作业,看着他头上斑驳的白发,我留下了深情的眼泪,老师改完最后一个本子,欣慰的合上了双眼,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作文到最后一定要升华。老师一定要批改完最后一个作业就死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修辞立其诚”。写任何东西,首先要感动的是你自己,感动的是真的,我经常跟良柱说,我们要把私人的情感转化公共情感。
小说里面我要表达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有可能我想表达的东西有点多,但小说写的可能又简单了,没有把我要表达的那么多东西表达出来。小说家一定要学会在作品里边留白,不是说在文本结构上你要空出,而是你不知道的,就不要去瞎猜。
我也不知道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因为我认识她是从回村的那一天开始的。我写小说特别慢,因为我要跟人物要建立感情,比如说我每天要花半个小时和颜素容对话,必须要在我的脑海里面清晰起来,建立了感情,我才会下笔去写她,在这之后才会小心翼翼,不能伤害她。所以小说里面从从未说过女生是干什么的,我不愿意去问她。
《蛊镇》里赵锦秀跟王木匠有一段激情戏,我知道这个事不能成,但我要找一个办法让激情无法继续下去,这个非常纠结,想了三个星期才想到办法。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像小时候从来不会去偷旁边有祖坟的庄稼,偷了怕受到诅咒。后来想等到两个人一发不可收的时候,突然看见他们家祖坟在那埋着,这事就无法继续了。这个办法必须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因此处理小说人物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爱惜,不管是好是坏,好坏是读者对人物的判断。作为一个作者,你的任务是把好人和坏人放在你情感的经纬度上去,做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因为在一个好的作家脑子里边不能有敌人。
你可以把蛊替换为其他东西,所有的民俗在我的小说里面,就是一个物品,他什么都不代表,文学最终要指向的不是物品,是人,是人此刻和物品共存时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说文学要表达是人此刻在哪儿,是什么样的状态,至于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不重要。
而放蛊最开始只是苗族同胞为了保护本族人的一种方式,其实把这些东西还原了,变到最后,它跟人的日常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说的这些真的不重要,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借助道具,我们可以回到人类最初的状态,我们要找的就是人最初的时候,刚开始出发的时候。
就像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当你爬到一个至高点的时候,你一定会停下来往回看。而文学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当这一段路要结束了,大家应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
陈老师:从修辞立其诚的角度,想请您为基础教育的语文老师就如何教学生写出真实的感人的作文提点建议。
肖江虹:我的妻子是一位语文老师。每次邻居或者有朋友的小孩来家里玩,就说我是个作家,让我教他们写作文。我说千万不要找我教,我也教不了,让杨老师教你写。
我教不了是因为他们的那一套完全是为了考试的。中学的作文可以教是因为它有规律,比如说它的议论文给你一个题目,把题目审好以后,从里边抽出一个论点,围绕这个论点把它表述清楚。还要要求掌握大量的资料,你起码得记住几个名人,那几个名人都说了什么话。一个小孩问我,他说我写作文老是记不住那些名人名言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自己编,只要这句话能够为你论点服务就行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中学生阶段要完成的还是要去完成。他要考试,就必须要在竞争的体制里边去适应。我们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最后要成为作家的,谁都拦不住他,但是成不了作家的,你怎么教也当不了作家。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我们把这句话的后半句的拿掉了,如果没有这1%的灵感,一切都是白搭。把任何事做到一个程度,真的需要天分。你把所有的小孩都放在同一个规则下去竞争,该脱颖而出的一样会脱颖而出。但该经历的他还是要经历,我们对孩子的担忧和焦虑有时候没必要,每个小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路。有一句话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能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我对他的提携和培养。现在小孩被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充斥着,我们以前的生活就是放牛。
现在的小孩比我们那个时候可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生活是跟这个世界是有关的。你能知道村里每一户人的名字,天黑了,你在村外凭着记忆,一点点的摸到家,哪个地方有个坑、有石头你是知道的。我在贵阳住那么多年,但楼上楼下邻居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也不知道。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现在很多作家的风景描写的能力丧失了,是因为他没有体察了,没有感受怎么写?小说永远都在对话,都追着人写,追着事写,看不到一点闲笔,这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郁闷,都有他的困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宿命,我们要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经营好日常,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黄朝猛:洞察的是人性背后的逻辑并思考怎么演化。
我读了肖老师的小说,刚才就一直在听,我在找一些问题的解答。我读的第一个故事是《傩面》。好多年没读小说了。读的时候,觉得我们贵州的作家能够写出这样水准的作品来,让我很惊讶。我非常喜欢余光中老师,他说你看一个作者就看他的文字给你的感觉,如果作者的文字都是没有感觉的、不负责任的、没有灵性的,你可以完全放心把它扔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多年不想读小说的原因。所以当我看了《傩面》开始的那几段,文字造型能力太强了,想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到第二天早上,就全部看完了。
这一段时间刚好我在看陈彥的《装台》,他以秦腔这样一个特殊题材为背景写了在底层的农民工、装台工人这样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同时还在看孙皓晖老师(《大秦帝国》作者)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他从文化的角度去挖掘,去审视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神秘文化。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肖老师《傩面》这个作品,也是表现了在特定环境当中这些人怎么想、怎么生存,还有你封面上讲,下一步他该怎么办?这里面思考就是一个人的生态问题,能够用贵州这方面具有特色的题材来表现那么一种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确实挺难得的,至少在中国文学园地当中从题材的独到性来讲,表现了别人没有表现的东西,让我感到很欣喜——这是读到《傩面》时的另一个惊喜。
同时我还在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专家组成员的著作,其中包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他是研究贫困状态的人的生存状态的首席专家,曾担任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并编撰过《人类发展报告》,同时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脱贫攻坚的相关研究和对策。对于贫困人群的生存状态,他是从宏观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你的《傩面》是从微观角度来透视一—我觉得,这是一个共鸣点,如果用他们专家组说的话来讲叫“交叠共识”。
无论是像孙皓晖老师从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角度,还是阿玛蒂亚•森他们从全世界宏观的角度,还是肖老师你从一群人一个地方一个特殊的生存状态的角度,都抵达了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读了以后还是挺有收获的。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进入,最终思考的都是人的命运状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可以以什么样的状态活在当下?
肖江虹: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人最终的走向和逻辑在哪里。
有一点讲得特别好,好的作家更多的不仅是记录者,还应该是预言家,知道人的最终的走向和逻辑在哪里,我们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判断的。优秀的以人为本的著作,其实不光像这种虚构的东西,比如像孟主席的写留守儿童的作品,其实是非虚构的,仍然有非常珍贵的社会价值在里面。我们现在的文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于显得特别的开放,不像以前把文学特别当回事,其实现在不把文学当回事的时候,文学才真正回到了最基本的原来的状态。
以前瞧不起写小说的,小说是旁门左道,所以你看人家写个《金瓶梅》都不敢说是自己写的,还搞个假名在上面,以前觉得写小说非常丢人,那时候诗词是正道。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文学特别包容,它是一种非常私人化,非常自我的劳动,当然劳动结果出来后能够有一批共鸣者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都匀这边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对这片土地认知的方式,跟我们认知的方式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述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贵州文学这几年慢慢形成一种特别好的现象,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群人是真的热爱文学,刚开始写作时,没有人想通过它去获利,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在写作的时候给自己的作品做一个预设的。作品写完发表后有它自己的命运,在没有发表之前你好好的经营它,让它的品质更好一点而已。
李杭兴:活在当下。
看了这本书,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惨,是生活的惨,生的惨,活的惨,死的也惨,我喜欢从文学里面看到生活。秦安顺说过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奔着死去活着,我们就为了死而活着”,我们是向死而生,既然生而为人,就活在当下,所以再怎么惨也要活着。
肖江虹:文学的功能是你在描绘天上的乌云后让人看到一抹亮光。
我觉得你像个哲学家,从来没有一个人用一个字就把我的小说概括了的。其实我的小说没有那么惨,我经常说一个作家写到最后应该把你的尖锐和对事物的态度隐起来,要把那种锋芒都灌注在文本后。以前特别关注太阳照着一棵树,喜欢写被太阳照射的一面,其实你要写太阳照不到的那面,那是所有人都看不见的。那种写法是生活上的简单,文学上的偷懒。
以前有个说法叫底层文学,大家都比惨,在我的小说《犯罪嫌疑人》中,里边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惨。但那个写法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奔着一种首先就有的概念去的。小说不能概念先行,其实在写小说之前都有一个想法,我们要把概念变成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一定是模糊的,是不可言说的。写完了小说,也未必能够用小说把你的想法真正表达清楚和表达完,而不是冲着一个非常粗暴简单的结论编几个人物,编一个故事,去完成自己要说的概念,这种写作是没有意义的。
好的小说一定是开放的,就像海明威说的,作者让你看到的是冰山的一角,但一定要把最宏阔、最巨大的部分表现出来,但你必须要让读者自己去揣摩,你不能言说。
文学到最后,做的是一种和解,剑拔弩张的部分过来以后开始慢慢的和解,写人和他人的和解、和这个世界的和解,但是这都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就是你要学会把概念和想法,通过别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给别人听。那些黑乎乎的场景不重要,你有能力在这个黑乎乎的屋子里边划一根火柴,这才重要。你要让读者找到出去的那道门在哪儿。文学的功能是你在描绘天上的乌云后让人看到一抹亮光。我们要把底层文学中肮脏的,惨的部分按住,把向阳的部分要表现出来。
文学早期的功能是娱乐,娱乐过后觉得应该赋予文学深意,慢慢的文学越来越沉重。我特别迷恋令人轻松的明清小说,我认为《聊斋》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好的短篇小说集,那种轻松随意里边还透着一种趣味。所以我经常跟良柱说文学是富有魅力的,文学应该回到最基本的姿态,不要把文学搞得那么苦大仇深,仿佛文学就是要呐喊、启蒙。
读者比作者高明多了,作家应该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以一种探讨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我跟读者之间是探讨的关系,而不是我要告诉读者道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我们可以分享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是这样认识的,我把它告诉你,你觉得我这样认知是不是对的,或者你赞不赞同我这种认知。
何世光老师他们那一代作家那么火,因为那个时候文学被无限的放大,一个作家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可以名动天下,那个时候信息是不对称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干嘛,唯一的途径就是定几份文学刊物,所有的信息都从这儿来。我爸那时候在中学里面做老师,学校里几个老师订刊物,你订一本我订一本,然后交换来看,所以信息不对称,老百姓只能从文学渠道知道国家即将要发生什么或者正在发生什么。
所以那时候作家承担的责任就是预言家,他知道未来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政策是什么,他提早把这些信息通过文学的方式传达给普通人,那时人们对作家顶礼膜拜是正常的。文学到了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但其实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文学只有被高估的,文学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写作到最后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即要学会构建崇高。现在很多作家没有构建崇高的能力,写不出好的、美的事,对于写坍塌的那部分特别厉害,因为不是每一个作家的内心都有崇高的意愿的,构建崇高是需要能力的。
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影响是让人平静,哪怕10分钟,就已经很厉害了,读完后不知怎样去言说这样一种感受,但心里像有一股暖流一样流淌,觉得这个世界原来还是有那么一些我们可能没注意到的美的微光的存在,我觉得就够了。
唐棱棱:感慨那种刻在骨子里、不需要别人去说教的对自然天地的敬畏。
各位嘉宾、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作者也坐在这里了,我很激动,可以面对面的去分享我的一些感受。我感触最深是《悬棺》里的人们和自然环境的共存,就是这些人和天地、鬼神、自然的虔诚和敬畏的态度。而这也恰恰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所缺少的很重要的东西。
特别是那段描写燕子集体殉崖的时候,乡民在岩石下面看着燕子的血洒在他们的身上,当时还有一段环境的烘托描写,只听到有人大喊一声“送喽”。读到这里,就觉得自己好像涌起了一腔热血,仿佛他们送走的不是燕子,而是至亲之人的逝去,那种刻在骨子里,不需要别人去说教的对自然天地的敬畏。现在的我们自诩是宇宙世界自然的主人,可以任意的去改造自然,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却忽略了土地如何在社会的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平衡。
就像书里肖老师说的“人类就是这样一程一程的往前赶,该逝去的终究要逝去”,现在不能理解的民风民俗,被认为是愚昧迷信的乡民,但他们确实是真实的存在过,也代表着我们最初的生存状态。我们现在的经济确实是发展了,社会也确实是发达了,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对土地的依赖。我们现在也应该像曾经的那些人一样,对自然界心存敬畏。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去平衡这种失去。
读书的过程过,看到很多环境描写的句子,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因为里面描写是贵州,那种乡音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和王老师一样,对于贵州出来的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是让人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王碧波:期待更多的人来言说这块土地。
从索良柱老师推荐贵州作家以后,发现居然还有那么耐读好读的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贵州的作品,像肖老师《傩面》的内容全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蛊术是神秘的,悬棺也是神秘的,傩面单是古老的面具就已经很神秘了,就是这些神秘吸引了我去读小说,关注小说。说到蛊,原来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但是看你写的蛊镇,我觉得蛊师可能就是草医。
这些东西本身就很神秘,不管你是借用道具将其联系起来也好,毕竟它是联系了,因此对我的吸引尤其深,这也是让我读下去的原因之一。另外是因为语言是贵州的方言让我读起来很顺口。从最初索老师带我们读贵州的作品,突然发现贵州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写。遗憾的是写的人太少了。对我这一生冲击最大的是我们去张达家,看到村里古老的风俗,他们唱的歌,都是值得写的。在这方面贵州是不是能多出一点能够站在我们自身的这块土地上的作家,描写我们整个生活。太期待这样的作家了。
孟学祥: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记录贵州的民俗,这种真正的把全部记录下来,也可能远远不够,而且我们在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写的不到位,所以你这么一说我们压力特别大。现在黔南这边的作家在做这件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深不深,做的好不好?但有了一个开头,我相信会有人做的好。
索良柱:孟主席很谦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他获骏马奖,他说他获这个奖是沾了我们民族的光,我觉得他讲的话特别低调。毕竟现在有了肖江红,有了冉正万,还有很多的作家都在努力,从零到一才是最困难的,从一到n可能要容易得多。
像我前面的讲座,我对贵州文学的一个判断,最起码我们现在能发出点贵州独特的声音,包括鲁奖为什么会颁给肖江虹?这绝不是没有缘由的。提名名单出来后,我问他怎么看,他说这个事情掉到你头上你就接着,没有掉到你的头上也不要有其他想法。我能听得出他这个话背后的意味,意思就是说这个奖极有可能不会颁给一个贵州作家。当时就跟他讲,我说这次应该是毫无疑问了,大可放心。提名的10位作家里面,他的知名度是最高的,《百鸟朝凤》的社会知名度已经使得不给他颁奖都成了问题了。
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要换一个方向来思考,我们跟文化大省是没办法比的,浙江的作家在国刊上发表文章仅70后的作家就有30位,而我们只有两位。我们现在是零零星星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肖江虹他们去做电影我就很高兴,特别是他那种格局,就是想把贵州的团队、贵州的人才全部聚到一起,把这个事情提到贵州文化建设的高度上来做,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看到有一年被称为贵州电影年,我们拍主旋律当然有欧阳黔森,艺术片有毕赣,纪录片有《四个春天》,商业片有《无名之辈》,好像一下子贵州在这几条道上都能起来,在电影上看到了希望。虽然我们在文学上滞后了,但后面我们也许可以有独特的东西出来。
文培伦:刚才说到的本土作家从地方进入中国。这本书是孟主席最新的作品《窑片》,就是我们牙周陶的纪实散文,明年春天的某月,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作品,走进牙周陶的前世今生。
肖江虹:孟主席在贵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里面,能够写成这样的没有几个人,他的特点是特别扎实,而且有很多年基层生活的经验。在乡镇里面做过书记,在州里面现在是文联副主席,他对整个贵州,特别是对黔南文化的、生态的、人文的都有很大贡献。特别是他写的关于留守儿童的《守望》,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好作家。其实我建议读书会下一步把孟主席的散文好好读一下,他小说写的也特别好。
袁鹏:刚刚我们讲到基层工作经验这一块,我其实就想问肖老师,我也了解您是贵州修文那一边的人。我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走过很多村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走进一个陌生的村庄,你对那里的人文、故事、人物都没办法靠近。我想知道在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像美术家写生一样,待在那里与他们相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了解一些人物。
另外是对您作品的感受,很多地方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比如王木匠,他本来一瘸一拐的,而你说他是腾云驾雾来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也会这样去调侃残疾人士,这种生活经验让我读到那里的时候会心的一笑。
我们写的是富有正能量的作品,也想学习一种比较扩展、比较记录化的写作,这一方面要向肖老师继续学习。
肖江虹:其实我们没有故乡,故乡是回不去的。而且所有的故乡都是记忆中一个曾经安顿过你的地方。我经常跟良柱讨论说我们对所谓故乡最大的认知就是你会发现故乡的前边还有故乡,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真的故乡在哪里。我们常说回故乡去,可故乡在哪儿?
我每年都会回故乡,特别是杀猪时,故乡的肉和市场里卖的肉不一样,随便做一下都很好吃,这是还能够找到的故乡,叫舌尖上的故乡。但已经消失的那些东西就找不到了。你问我写的东西是否和故乡有关?有一点关系,又不完全有关系。脑子里面构筑的世界,它是一个全新的。为了拍电影《傩面》,我几乎把贵州的所有县份走完了,却没有找到我理想中房子的排布。最后在遵义播州找到了特别相似的排布,十分兴奋。
就像我写《傩面》一样,最早的时候是去安顺,安顺的地戏也是属于傩戏的一支。到安顺后,发现地戏跟文学是没有关系,安顺的叫军傩,他有曲目的。是文工团专门演给那些士兵看的。后来到遵义道真,铜仁德江,看了以后,找到了傩戏,因为它跟生死有联系,与另一个世界有联系,傩面师戴上面具是神,摘下傩面就是人,它可以接两个维度之间的人,打通后傩戏就属于文学范畴了。
说实话,我们一群作家去采风是没有意义的,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都无所谓,图的是晚饭的酒。我们可以几个坐在酒桌上聊文学,非常虔诚的聊文学。那时大家都刚上道,就特别喜欢表达,那时的想法特别了不起,正处于文学的青春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老了以后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青春期的那段记忆是非常深刻的。那种非常融洽的非常自由的交流,恰恰是刚上道的人之间的碰撞,特别有价值、有意义。
所以写一个东西,是你骨子里要写的对东西的深层次的认知,如果你要写具体的事,田野调查就要做得非常扎实。为了写《傩面》,我收集了很多傩戏的唱词。第一次知道跨过水井和灶台是一种罪。里面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文化,你要写就要对它的认知要到那个层面,到了那个层面,才能和自己以往写的东西不一样。
我刚写完一个小说,叫《美学原理》,其实小说跟美学真没什么关系。在一次和大学老师的聊天过程中,他们说你的小说我不太能读得懂,但关于美学的那些话语的判断几乎没问题。
文培伦:因为我们的年会已经后延了一个小时,所以只能就这样嘎然而止了,至诚谢谢两位嘉宾:肖江虹老师和索良柱老师!
肖江虹:不要鼓掌,我最后再说一句:说老实话我觉得没说够,很少遇见那么专业的读者,有机会我和良柱我们再来,谢谢大家!
(文章摘自:崇实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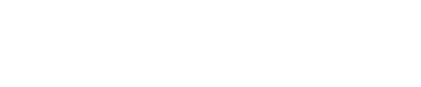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