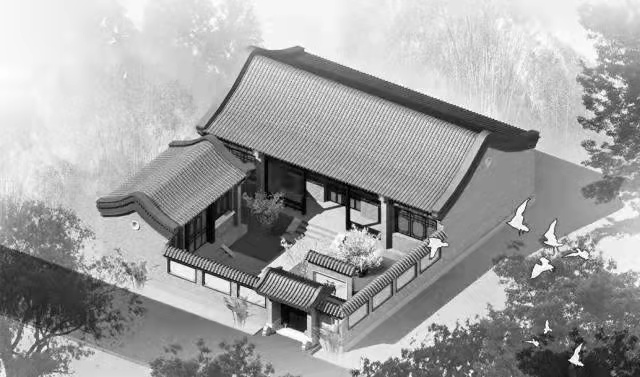
东门是安龙老城正东的一道城门,古称“朝阳门”。安龙人对这一带的地名有严格的区分,城门外称“东门口”,城门内称“东门里头”。虽然城门早已不存在,但是人们心中的东门却永存,有人还亲切地在“东门”二字前加了一个“老”字。比如有人问:“你家住哪点?”答曰:“老东门口。”或:“老东门里头。”口气中洋溢着对这块故地的情和爱。
东门的造型是十分严谨的,大约是三尺长两尺宽的六面方石垒砌而成。据老人们传说,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其黏连剂是用糯米稀饭掺石灰浆做成的。我的天,从桅峰山沿龙井山下老东门,到北门、小西门、大西门,再回到桅峰山。这么一大圈城墙,史书上记载:“长1203丈,高1丈5尺,底宽1丈,上宽7尺。”这要多少糯米来煮稀饭啊?真是小人不识王者气。老东门的城楼是十分威严的,青石墙、梓木柱、黑筒瓦,四个翘角上挂着风铃,屋顶上一杆旗。但我未见过旗的样子,只有那风铃声还残留耳际。那两扇城门蛮大蛮厚,门上栽钉了许多包包凸凸的铜钉,特显雄奇壮观。后来我到北京天安门开了眼界:“我的天啊,我们安龙的老东门、小西门、大西门不也如此这般吗!”心中顿生几分自豪。也许是得益于那口老祖宗发掘的珍珠泉(东边龙井)的灵气,流水泱泱,育人润物;也许是得利于东门城墙脚下那块鼠场坝的宽宏大量,商贸兴旺,财源滚滚;也许是城门内徐家祖上一介雄师在盘江八属打擂台打出朝廷赏赐的《武魁》大匾的神韵;也许是东门内的天主堂及教会学校潜移默化了西方的文明因子。也许就没有什么“也许”,就是老东门内外芸芸众生世代的造化,使他们在这块热土上兴起了自己的手工业园区。东门口的粉坊、碾坊、榨坊,东门里头的染坊、酱菜坊和烤酒坊应运而生,与时而兴,被坊间称为安龙手工业“六坊”,经济学家誉为“安龙传统工业的窗口”。
笔者童年时代在这里的教会学校(圣心小学)读过书,中学时代又交了几位家住这一带的朋友,比如杨永国、江福泽、詹小春、王小永、徐复胜等,加之时为家中生意场上的跑腿,常到这一带交账和收账,所以耳闻目睹这“六坊”的营生概况,现在将其回忆记录下来,献给读者一段老东门内外尘封的故事。
粉坊
在东门口至东边龙井之间,有一片肥沃的土地。从龙井流出的一汪泉水,通过城墙脚的涵洞,一路欢歌流过其间,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天然水渠。后来,人们怕它不断“蚕食”这里有限的土地,就用石头在两岸砌了堡坎,把放任的流水规守在一定的范围内。岸壁收缩了,水则变深了,容量也变大了,原来不规则的东门渠变成了东门河,保证了这一带农田菜地充足的水源。
据说,此间的宋、谢、陈几户人家祖辈是随明代朱元璋“调北征南”战略,而从江南水乡迁徙过来的。得此良好水土之灵气,其世传的造粉工艺便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们造土屋,制石磨,养土马,购土豆(指小豆、豌豆、蚕豆、黄豆等)。用龙井水泡豆,过滤选豆,驾辕磨豆,然后搅拌豆末成豆粉坨,再将粉坨放入木榨,通过人工绞动转盘,一排排白色细匀的粉条便源源流出,像一道道银丝,煞是喜人。如此这般,银白色的粉丝便流淌在一根根竹竿上,继而再将竹竿上的粉丝架到屋外广场的木架上晾干。如果说作坊内是清水泡绿豆儿,石磨碾绿豆末儿,土榨压粉坨粑儿,那么,坊外则是另一道景观:阳光下,银丝晃,微风拂,白布扬,好一派白色风光。在东门外的粉坊里,每到晒粉丝的日子,那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竿竿粉丝插入木架上方的孔洞,一排排插满粉竿的木架,横成排,纵成行,宛如一支受阅的海军方队,容光焕然,英姿勃勃,美不胜收。假若我将这景画成一幅油画,画名就题“银浪排空”;假若将这风景画成一幅国画,题词则是“谁移云海此间来”。
晒得两日,竹竿上的软丝就变成了干而脆的丝条,然后轻轻取下,放上案板,按一定的长度和重量打成粉条包,销往城乡八地,还远销云桂川渝,成了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道佳肴。它的食法,或炒、或汤、或拌,或做包子、饺子的馅儿。驰名中外的一道川黔菜叫“蚂蚁上树”,“蚂蚁”是瘦肉丁,这“树”正是粉条。什锦火锅中的一锦也是粉条。“凉拌三丝”中的一丝也是粉条。
我同学宋庭渊家的粉坊有五大特点:开办最早,规模最大,产量最高,质量最好,销路最远(从两广出口南洋)。他子承父业。人家毕竟是书香门第(其祖上宋杰是张之洞同窗,宋绍锡、宋之洵均是清末民初安龙乡贤乡绅),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动脑筋谋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技术上做了重大改革,将所有人力和蓄力的劳动全部改成了电动,将作坊的空间拓宽,安装了机器,变成了机磨车间,榨粉机由木质改为铁质,原料也由豆类变成了豆芋混制,不仅降低了成本,还使粉丝的质量变精变细,产量翻了几番。当年,宋氏粉坊与毗邻的谢氏、陈氏粉坊被统称为“东门口粉坊”,加上龙广镇顾屯的几家粉坊,被称为安龙粉丝的“两大基地”。生产发达,生意兴隆,撑起黔西南州粉条生产的半边天。
碾坊
出东门,向正东前行约100米,一座年陈久远的石凸桥横架于此,人们叫它东门桥。从东边龙井流出的泉水,通过粉房头的小河从桥下流过,哗啦啦,日夜不停,四季不息。不知何年何月,一位姓肃的能工巧匠便慧眼认准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便破土采石,伐木丁丁,斧锯声声,砌墙造房,不久,一座碾坊在此落成,碾坊的动力源就是这股造福的龙井水。
记得儿时常到此地玩嘘水枪。将自制的竹筒对准碾坊外面小河中一处比较平静的流水,抽动几下用筷子做的轴,水枪中就装满了“子弹”,几个顽童互相对射,射得满身湿透后不敢回家。咋办?守在水沟边看水流,混时间等衣干。但见水从桥下流过后落入另一道水沟,水沟下面被挖得深深的,架着一个直径约3米的水车。水车的车轮由几十块长条木板组成,俗称“龙骨板”,非常形象。水车的“龙骨板”被高处落下来的水所冲击,一片“龙骨”带动栉比的另一片“龙骨”,水车就轱辘轱辘地转动起来,那水流溅起的五彩水泡和奇丽水花就是我们的欢乐,那不停转运的“龙骨车”就是我们的游戏机,如果谁丢下去的一片树叶轮回一周后还能再转回来,那么就等于中了奖,乐得直叫:“那片叶子是我的!”如此争先恐后地丢叶子、看碾子、找乐子,乐此不疲、乐不思蜀。
至于这水车转动而带动水碾碾米的精彩情景,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为什么?碾坊的主人不准娃娃进入碾坊,一怕出事,二怕影响活路(当然应该叫怕影响工作)。不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有一年临近过年一个赶鼠场天的中午,我爹在场坝上买了两斗糯谷,准备碾成米用来打饵块粑和包粽子。他请一个“扁担”挑进碾坊排“轮子”,我自告奋勇:“我去守。”然后就跟着进去了,任务是守在麻布口袋旁,随着“轮子”慢慢移动谷子。在这排轮子的时间里,我把碾坊的内容看了个明明白白。
原来如此啊!外面那个水车的转动就带动了碾槽上那个石磙子的滚动,那个石磙子少说也有千把斤,它在半圆形的石槽中慢慢滚动的转程,也就是碾米的过程,准确点讲应该是碾谷子的过程。碾槽的声音非常单调,车来车去就是“哧哧”和“嚓嚓”,一点也不吸引人。无聊时,我把注意力转向那位管碾子的师傅。那人四十来岁,三角眼,瘌痢头,说话有点“呷”,把“水”说成“腿”,把“碾米”说成“点咪”,恶声丧气没有半点笑容,很怕人的。他手中提着一截竹竿,两眼一会儿望望碾子外面的水车,一会儿又掉过头来看看碾槽里的动静,还不时用手抓起一撮碾物抡抡捻捻看看,随时掌握“火候”,看得出,怕人归怕人,人家责任心是很强的啊。当他认定已达目的后,会高喊一声:“×家的米碾好,接口袋!”这时,他就刹住碾子,在碾槽上打开一个口子,×家的人就在口子处打开口袋接自家的碾物,再拿到一旁的风车里吹簸,从风车嘴吐出的是糙米。被风车从另一个口吹出去的是老糠(也叫粗糠)。接好糙米后再排一次轮子,等“瘌痢头”师傅,再开碾一次,再拿到风车处吹簸一次,这样簸出的二道米才叫正米,扬弃的叫细糠,这细糠是喂猪的精饲料,前面的粗糠只能做燃料。我在碾坊里等了近三小时,老爹才找来一根扁担挑糯米。回家路上,我问父亲:“碾坊不收钱吗?”“不收,他吃哪样?那些粗糠、细糠不是钱呀?!”啊,明白了!
三小时,我从好奇到厌烦,但因“进过碾坊,见过碾米”,获得了在小朋友中显摆的谈资:“我给你们讲,老东门口那个碾坊碾米是弄个的……”
榨坊
我与老东门内的徐氏兄弟复胜、赐功是圣心小学的同学,放学后常同他们在城墙上玩。我们登上城楼,在城墙上向北行,大约250米后下到新东门。此处名叫新东门,其实就是20世纪40年代为市民出入方便而破城墙开的一个路口,有口无门,只不过大家都这么叫罢了。
我们下新东门后,寻着油香而去,直奔秦家油榨坊去看他打榨油的把戏。因为在城墙上能看见秦家油榨坊冒出的炊烟,更能闻到菜油的香味。很久以来,每到这一带就想进去看个究竟,苦于没有熟人带引,怕被人家“方”出来。徐同学认识榨坊老板家娃娃,他扯个谎,说一声“找秦小牛”,我们也就混进去了。
这是一幢十二柱四大间的草房,坐落在鼠场坝的北头(现在县文化局的正门口)。我们进门后,一阵菜油香扑面而来,五个打着光胴胴的汉子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有两个守在一口大铁锅前,手持大锅铲,不停地翻炒着锅里的菜籽,锅下的柴火燃着冲底的熊熊火光,锅里的菜籽受热后爆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据常来这里玩的徐同学说,这是榨油的第一道工序,叫炒籽,最重要的是把握火候,火小了炒的时间长,且炒不透,榨不出大油;火大了,容易煳,榨出来的油就成带煳味的次品。所以又管烧火又管炒籽的工人被称为师傅,只管炒籽或只管烧火的那算下手,被称为伙计。那师傅三十多岁,据说,十四岁就到这家榨坊学徒,很勤快,吃得苦,又细心,伙儿也晃,老板把自家女儿许配给了他,成了上门女婿,并且成了二老板,榨坊里的活路全由他料理,老板只管买进卖出。
另外三个四十来岁的伙计互换着打撞杆,这道活真有看头。我们进去时,他们已将炒熟的菜籽打成圆饼安到了榨机上,一个紧贴着一个,圆辘辘地排成一排。其中一个伙计守在油桶边负责加楔子和接油,另两个负责打撞杆。撞杆是一根结实的圆木,一般选硬朗的杂木做成,约有一丈长,粗如大碗口,手握的一端叫撞尾,略细,被握磨得油光油光的,另一端粗一些,顶头被撞成了“葵花盘”状,撞杆的中间系扎着一根结实的棕绳,绳头捆扎在房梁上,悬在空中。这师傅知道,凡是进榨坊来的人多为来看他“打撞杆”的把式表演,所以非常得意,人越多,他的劲头越足。他们俩双手握紧撞尾,先退后到吊绳允许的境地,然后一哈气带小跑步,并逐步加快速度。两人配合默契,步调一致,四只眼睛瞄准撞靶,待那撞杆快抵进“靶子”时,同时使劲“嗨——”的一声大吼,那撞头与“靶子”相碰发出“咚”的一声巨响,一排木楔子便抵进了几分,再如此反复几个撞击,榨槽里的油饼便挤出淙淙的油滴,随着他不停的撞击,这油滴由点变成线,由线变成股,从光滑的木槽流入油桶。这打撞杆是个拼体力的活,连撞十来杆就得停下来休息片刻,喝口茶,咂袋烟,提提神。另一位师傅乘此再往榨槽挡头加楔子,抡起八磅大锤使劲往里打,待打到不能再进的位置后,他便向打撞杆的师傅吼一声:“好喽!”两位师傅起身握起撞杆,又开始“嗨”起来。“嗨”到一定的程度,就算榨到底了,只等油饼中榨出的油慢慢流入油桶,然后一一退出楔子,再一一取出已榨干的油枯饼堆放在一旁,铁锅边的两位师徒再向榨中安放第二榨菜籽饼。
在油榨机边上,那工人专门负责将一桶桶接满的油提起,走向库房,将油倒进大大的瓦缸中,等老板出售给菜油零售商。当然,也接纳零星客户交菜籽来打油的活计,按斤计价,油饼留给榨坊。也做用菜籽换菜油的小生意,只要有钱赚,老板是来者不拒的。据说,这榨坊主人还在老东门那面种有一片菜地,这油枯便成了种菜的上等肥料,所以他家上市的白菜、萝卜,又大又嫩,十分抢手。有人说他家“又吃肉又泡汤,日子过得响当当”。
看完榨油坊中全过程的工艺表演,我突生奢望,奓起胆子向那位打撞杆的师傅提了个小小的要求:“师傅能不能送我一坨油枯?”我试探着问他。
拿去整啷子?”他问。
“钓鱼喂窝子。”我答。
“那是要钱的咧!”师傅伸出手比画“五分钱一张饼”。
“我没有钱啊,只要一小坨嘛。”我继续向他蘑菇。
“像弄个吧,你起码是个五六年级的学生。我打个猜子,你猜着了,就送你半块。”撞杆师傅与我较真起来。
我说:“可以嘛,试试瞧。”
“听好!”他出了谜面,“大斗挤小头,小头挤里头,实在挤不进,眼泪和尿一起流。”他得意地望着我们几个,命令似的喊: “猜!”我们几个互相咬咬耳朵,几个推我答,我说:“是不是打榨油?”“上街买毡帽——对头!”他马上将一块油饼掰成三坨,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坨。这一天,我们也是又吃肉又泡汤啊,各自高兴而归。

染坊
当我看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时,那一匹匹从楼上往下吊晒的染布景观,非常大气,非常别致,便想起老家老东门里头王家染坊的情景。
王家染坊离东门不到100米,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和手艺。掌门人是我小学同学王定芬的父亲和大哥王明远、二哥王明义。王家染坊坐落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内,两边厢房里分别安放着两口木质的大染缸和七八口大瓦缸。那大木缸的口径约两米,缸高在两米之上,用木块镶就,像一只放大了的水桶,木工工艺上乘,木块之间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缸内装了半缸用本地产的蓝靛泡制成的蓝色染料,发出轻微的腐叶味,但不刺鼻。两口大染缸各有功能,一染单蓝,另一缸染双蓝,配料不同,浓度不同,价位也不同。另一间厢房安放七八口大瓦缸,安龙人叫半截缸,出自安龙龙头大山脚下的北乡(今龙山乡)老窑。里面存着王大伯按祖传秘方配制的染济,缸口用油布封得严严实实,缸上标有甲乙丙丁符号。
他家正房分为三间,一间为调料房,架着一口大铁锅,用来熬制蓝靛。蓝靛用大山深处生长的一种阔叶乔木的叶子加工而成,民间叫蓝靛木,干壮叶茂,乡间大树林中常见。山民将其落叶扫拢,放入池中腐蚀而成,是染坊必用之料,也是农民挑进城换点油盐钱的一种资源。熬靛是个精细的配料活,染布的质量取决于这一关,所以这就是王大伯秘传给王定芬两个哥哥的,多少斤蓝靛配多少两白矾和多少两定色料,这是坊间的工艺秘密,只有王家父子知晓。我的同学、王家幺妹王定芬说:“不能问,问了也不告诉你。”是啊,过去的祖传工艺都是“传子不传女”嘛。据说,他配料多在深夜悄悄地进行。火候也有讲究,而且不好具体言传,只有自己在失败中摸索标准。因而,坊间有“十家染坊十个色,十个师傅不同格”之说。当把染料配好、熬匀后,第二天才分别舀入大染缸。正房的一间堆放着待染的白布,上面标有主人姓名、布的长度、单蓝或双蓝的要求及取货时间。另一间则摆着已染好并经过石磙子碾平的染成品,折叠得整整齐齐。取货的人一到,递过条,报个姓名,王大嫂或王二嫂就迅速对号收钱交货。
王家两哥弟体魄健壮,个头又高,负责操作染缸中的浸、染、扭、漂、碾等既要体力又讲技术的活计。那一人多高的大染缸,操作时得先上几台木梯,然后再哈着腰、埋下头,用双手在缸中进行搅、压、挤、翻,一招稍不到位,那染出来的不是清一色的单蓝或者双蓝色,而成了“斑蓝花布”,就是废品,客户是要索赔的。因此,王家配料和操作染缸的主活不请外人,全是王氏兄弟自己动手。原因有二。一是怕色泽质量不到位,影响信誉影响生意;二是怕教会徒弟,自己丢了饭碗。所谓“单蓝”就是只染一道,“双蓝”就是等第一道染透、晾干后再进另一口缸染第二道。单蓝色质浅褪色快,双蓝的色质重,“经饿”。用王家的话来说:“单蓝单蓝,三浆两洗蓝不蓝。双蓝双蓝,烂成刷刷蓝还蓝。”自然一分钱一分货啰,双蓝的工价是单蓝的双倍。
经过一浸二泡三染四扭等工序之后,这一染缸的几十匹布才算染好,然后将其取出,用一根棒棒当绞棍,左绞右扭,将染料滴回染缸,再将布装入竹篮,顾来几个临时工挑到鼠场坝的小河中洗漂。当那几竹篮布匹倒入小河之后,顿时那一潮清水就变得蓝莹莹的,摇摇荡荡地流向磨园头的河沟深处。当时大家不懂什么叫污染,所以也无人出来干涉管理,任其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如此将清流变成蓝水,不过,那东边龙井源源不断的水流,很快就将它冲淡,忽儿又恢复了清澈,这里得借用一个形容词:得天独厚!
将漂洗后过的布匹挑回来后,王家大人及小工一齐行动起来,将一匹匹长约3丈、宽2尺的湿布从楼上搭到天井的竹竿上,那布头一直拖到离地不远的下方,一条条,一排排,层层密密,把个天井布置成了一个美丽的蓝色森林。这景观正是本文开篇赞美的张氏电影所追求的那种大场面、大写意、大视角、大气势的审美效果。不过,我敢肯定,当年王家几代人并不懂得张大师所追求的美学,他们追求的只是票子和日子。不信,你去问问健在的王家兄妹。
离王氏染坊约200米的府后街口,也开着一家染坊,坊主姓樊,染坊规模也挺大的。东门里头这王、樊二家染坊算是安龙染坊业的老字号了,半城人穿的衣服多出自他们的染缸。
酱坊
“酱坊”,即酱园,制造并出售酱、酱油、酱菜等的作坊。《现代汉语词典》如此解释。
在离王家染坊不远的老东门和新东门之间有一条巷子,从牛黄街口进去,直抵城墙脚,小地名叫义仓街,是一个菜农与居民杂居的地方。在众多的瓦房、草房、菜地之间坐落着一个四合大院,宅主姓李,人称“李总办”,是民国初年县里一个管厘金的总负责人,有点像现今的县税务局局长。志书记载,清末时期,安龙县当局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坡脚渡口和白水河南渡口设立了厘金关卡,对进出货物征收厘金,因此建立了厘金局,李总办即是民国时期的一任厘金总负责办理人。据老人讲,李家这个酱坊历史有点久远,是李总办的父辈开创的,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跟安龙的诸多手工作坊一样,没有自己的品牌字号,这是安龙老辈们的认识观念问题,只知埋头生产和经营,不懂得打“招牌”和做广告的重要性。你看,在文化发达的京津沪,人家开个涮羊肉店,就取个“东来顺”“南来顺”什么的店名,又好听,又吉利;开个包子店就取个“狗不理”店名,以怪图利;上海炸五香兰花豆小店也取个“城煌庙五香兰花豆”,多么气派。好在那些年,安龙城池不大,人口不多,一说“李总办家的酱油”“李总办家的大头菜”,家喻户晓,“啊,义仓街那点”“啊,老东门里头城墙脚”“徐建堂一传锣,两声叫,张家王家都知道”,这即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安龙城空间的形象写照。
这个李家酱坊我很熟悉,不仅是常去打酱油,买酸梨子、霉豆腐,而且认识他家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李怀碧,她是李总办家大女儿,从贵阳读师范毕业后回老家当老师,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板书),满腹经纶,讲课时就引经据典,但是不讲国语,都说方言,比如把“铅笔”读成“沿笔”,把“做事”读成“住事”。再一个是李老师的弟弟李开兴,读安龙中学时,他高我两级,个子高,球技好,曾参加兴义专区中学生篮球队征战贵阳,后来在兴义教书,定居兴义。鉴于这两层关系,读初中时的假期,我曾几次到家酱坊做过小工,对这里的景象和生产情况至今难忘。
李家酱坊有三大标记。
第一是宽敞的两个晒坝。一个是他家的四合天井,一个是他家的后园。这两个地方排放着许多的半截缸和大龙坛,全是本县北乡(今尤山)土窑所产的土陶瓷制品,半截缸里腌制的是豆类酱品:豆瓣酱、豆豉颗、霉豆腐、豆油(酱油)等。缸口用油纸封口,还盖上篾帽(斗笠)。当太阳天即敞开曝晒,让缸中之物充分发酵;当阴天盖上篾帽,揭开油纸,让它晾;当雨天则戴上篾帽让它囤。经过一番夏日秋雨,缸中所腌的豆制物才出色、生味、溢香四面八方。因此,坊间有说:“不曝九十九,豆酱卖不走。”大龙坛里腌的是盐菜、酸菜、泡菜、泡椒等水食货,坛口用一个外面套猪尿脬的稻草塞子塞紧,除师傅之外,别人不能乱动,一怕敞气,二怕污物落入。1956年搞公私合营后,将这两晒坝称为“晒晾车间”。
第二是成排成行的竹架和木架。为什么要用“成排成行”这个词?因为李家晒坝四边的木架和竹架很整齐,整齐得像军营中的队列方队。当过兵的人都懂,在军营中进行队列训练时,教官的一个起码要求就是“横看成排,纵看成行”。李家晒坝的竹木晒架正如此,说不定他家请的师傅是个退伍军人呢。1954年的寒假,我和小敢生在他家做小工,就是在这位严格的师傅手下干活。他要求,长萝卜切成条条、圆萝卜切成桠桠,用棕叶绳拴好,八条一串,四桠一提,挂上架时,一律头向上,看起来就像一架架的白玉,美极了。切大头菜时,先连叶子洗干净,再连叶带果一破四桠,但是“断头不断尾”。这样,就不用绳拴,把它分开后“骑”在竹竿上,叶子朝天,看起来像一行行绿色的翡翠;洗净的青菜,不切,不拴,一匹一匹地搭在竿竿上,看上去好像一个个身着绿色运动衫的体操运动员在单杠上做弯腰动作。小敢生是个美术爱好者,干完活后,他就拿出纸笔将这个景观画下来,开学后他交给教美术的龚老师看。龚老师说:“不错,下次美术课我带你们去李家酱园上写生课。”
第三是古色古香的铺面。李家的酱菜制品,主要是批发给零售商,自家也开的有一个铺子,就在他家朝门一侧。“门市部主任”就是李开兴的妈妈,都叫他李伯妈,一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中年妇女,衣着得体,满面慈祥,忠于职守。货架上和柜台上摆的家什多是景德镇产的青花瓷器皿,有钵钵、瓶瓶、罐罐、罂罂,这些主要是装干的和半干半汤的腌制品。还有几个玻璃坛坛,主要装酸辣椒、水豆豉、泡萝卜、藠头、泡大蒜等水腌制品。靠墙的货架上则是专卖空瓶空罐,有景德镇产的精品,也有本县北乡产的名品,供人买回去自制酱菜时使用。整个铺面给人的观感就是八个字:整齐、美观、大方、卫生,看上去清清爽爽,明明净净,一则吸人味蕾,二则让人放心。有些与李妈熟悉的人当面夸她:“你这个铺子呀就跟你这个老板娘一样,干净体面。”她呵呵一笑:“卖吃食的嘛,就要让人家买个干净、买个放心啊!”
李伯妈不仅做三分两文打醋打酱油之类的小生意,几百几千大宗的批发和进料的生意也是她大权独揽。1956年全县搞公私合营后,他家的酱坊并入县酱菜厂,李妈成了厂里的一名职工。这位老人在“运动”中吃了不少苦,但她从不计较,乐观对待,难怪人家能活到九十多岁,心宽寿延呗!
杨家酒坊
乡友,曾记否?硫磺街上重酒味,不花一文钱,可获三分醉。乡友,不会忘,杨家门前闻酒香,不论春夏与秋冬,路人个个看酒缸。当我回忆老东门内的硫磺街时,想起了王家染坊、李家酱坊,洋人办的天主堂,若瑟医院的修道和孃孃,还有杨家的烤酒坊。
谁说得清,曾经被遗忘的角落留下的老屋老树、老街老井,而今成了重点保护文物,有的甚至上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硫磺街,曾经因天主堂的洋派和若瑟医院的免费看病,加之几家土制作坊而热闹过一些年头,没有人嫌弃那里东倒西歪的木壁石墙瓦房,没有人诅咒那狭窄石板路上的“眨眼石”弄脏了他的衣裳,夜深人静加之黑灯瞎火,却没有人编传这方的“聊斋”鬼事,你说为什么?有人说是得力于老东门的神威,有人说是因为珍珠泉那水的圣洁,也有人说是龙井山和龙井庙那神灵镇了一方邪恶。说不清,仁智各见。反正当年硫磺街很窄很小,很土很老,但很热闹,很干净,很安全。
对于我这个曾经在这里的圣心小学读过一年书,又因家事多次出入若瑟医院和杨家烤酒坊的“察街差”来说,杨家烤酒坊的映像挥之不去。原因多啦:一则我父亲与杨家酒坊的掌门人杨二耶常有生意上的交情;二则我父亲钟爱他家酿造的纯香米酒,打酒之事我常为;三则我姐傅汝玲与杨家女杨庭碧是小学时的闺密,为她们传递书物或夜晚去杨家接我姐也是常事。如此一来二去,对杨家酒坊知之不少。
杨家祖上在硫磺街置了大片地建造酒坊,正房属传统式的大三间,面对硫磺街正中,后为左右厢房,中是院坝,直抵老东门北侧城墙脚的大园子。好大一片啊,多少面积不得而知。
应该说杨家酒坊是当时老城一个自成一条龙生产线的手工业典型范例。
杨家当街老屋与老城传统老屋结构相似,石铺台、厚木门、半截幺门,两侧分别为居室和铺子,中间为堂屋,木方“海”的楼板,楼上一般不住人而做杂物间。
每走到他家门口,一阵酒香扑鼻,两个酒坛显眼。这酒坛亦称老坛、龙坛,出自本县与贞丰接壤的北乡(今龙之乡)的坛罐窑,属里外涂釉彩的优质土陶瓷制品,泛着光泽,成V字形。胸径宽处50厘米,坛高约100厘米,雄踞于堂屋与铺子之间的柜台一旁,便于主人卖酒,也便于进屋沽酒和饮酒客人取酒。这大酒坛每只可盛酒百斤。坛口约15厘米,用一个晒干绷直的猪尿脬包裹着干稻草做成U状的塞子,把坛口塞得紧紧的,打开时发出“嗡”的一声。主人量酒时,用冰铁制成的提子从坛中一提一提地打,这提子分五钱、一两、二两、半斤四种容量规格。生意场上适兴“快打酒,慢提油”的手法,说,快打的酒,酒泡泡可以溢边,而且提得越快,冒起的酒泡泡就越多,看起来满满的,实则不满。卖油人打油时,得慢慢地提,让提起来时溢出的油慢慢滴回桶中,看起来满满的,实则也不满,行行都有学问呢。杨家出于祖传的良好商德,一反常态:慢打酒,注重钱饱货足。有位持怀疑态度的酒客硬是要考验考验,他递过酒瓶时说,“我这瓶子一斤酒刚刚满瓶口,请你用五钱的打两提,用一两的打两提,用二两的打一提,再用半斤的打一提,看看如何?”杨家人如求照办,六提打完,不多不少,正齐瓶口。这酒客服了:“从此我就醉在你家了!”
杨家酒坊的精彩在正房之后的院坝两侧。
左厢房常是热气腾腾的局面。一口大铁锅上的大甑子蒸着糯米或者苞谷,炉灶里热火朝天,甑子上蒸气袅袅。与此彼邻的另一个大灶上架着一口天地锅,锅内是已经发酵的糯米或苞谷,一支小竹管一头接在天地锅内,一头接入酒坛,经灶内文火烤蒸,晶莹剔透的蒸馏水(酒)渐入酒坛,温温的、甜甜的、香香的。不懂酒的孩子闻着那味道,耐不住时,会向酿酒师讨一口,师傅也不吝啬,顺手将小杯盛一点递给他,亲切地说:“只能闻一闻,最多舔一口,温酒会伤头!”
另有几名工人在另一栋厢房忙碌着,有的将接满酒的大龙坛密封好,搬来草帘、棉絮将之捂严,让其窑藏起来。有的在用大木棒搅动瓦缸中蒸好的糯米或包谷,细心地往瓦缸里施撒酒药(曲药或酒曲)。有的在挑酒糟煮猪食喂猪。各司其责,忙而不乱。
院坝后面是相连的三间猪厩,分养着小猪、架子猪和肥猪,大大小小十七八头。它们在猪槽里,“吧嗒吧嗒”地抢食,够火的。平均一月出槽(卖掉)一头,这收入可丰啊!
猪厩下面是四五尺深一丈多宽的猪粪池。别小看这不美观的地方,每年开春之后,种苞谷的农民会上门来买猪粪做点苞谷的底肥。来人取根竹竿插入粪池,然后再量量粪池的长宽,皱皱眉头,他便算了个大概。经与杨家一阵阵讨价还价,谈妥后,组织几个壮劳力,挑上大大的粪桶,一天就挑光。你说,这人与人之间,人与牲畜之间,牲畜与庄稼汉之间,庄稼汉与庄稼之间,不就是一个互相依靠的生存链吗。如不是庄稼人的需要,杨家还得花钱雇人来清理粪池搞卫生呢。
杨家酒坊的产销和酿酒的连环工艺,放大点说,就是一个大企业的产业链啊,这大企业的董事长、第三产业开发部经理,全被杨家两个老人包了。
出酒这天,两个老人格外忙碌,杨伯妈着手装酒、封酒、窑酒等事宜。杨大伯也有个特殊任务。酒房里靠墙的地方排着一排笋壶(一种土陶容器),上面拴着写有姓名和数量的白布条,杨大伯一个个接好酒再放回原处,老主顾按时前来付钱取酒。有人说,杨家酒好不上街,大小笋壶排成排,三斤五斤提前定,酒客接二连三来。
注 节选自《荷城旧事》第一篇“城墙内外”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